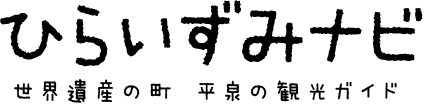「兵共夢跡」中津 文彦
我第一次到平泉是1945年的秋天——奇怪的是我竟然記得如此清楚。那是我滿四週歲前2、3個月的事,要說不可思議也的確有道理,但我清楚記得這些是有緣由的。
我依然記得戰爭結束前後的一些零零碎碎的事,或許是因為我童心照樣感受到了異樣的氛圍吧。
8月15日,正是一關的盛夏之際,晴空萬里,烈日炎炎。我正在院子的柿樹下玩耍,母親走到我身邊,伸出雙手抱住我的頭說:「你爸爸要回來了,太好了」,這句話嘟嘟噥噥地反覆說了好幾遍。母親也許是從收音機裡聽到戰爭結束的消息了吧。
當時父親是舊制花卷中學的教師,戰爭結束前半年左右被徵召入伍;用過去的話說就是「被抓壯丁抓走了」,萬幸的是父親還留在日本國內,但我想母親一定十分擔心他的處境。
在那以後又過了半個月, 9月初父親復原回家了;那個時代電話、書信往來極不方便,事前也沒有任何音信,我還記得一個黑漆漆的男子忽然閃進家門緊緊握住母親雙手的情形。
如今雙親均已過世,也沒法考證後來父親為什麼不想恢復原來的教職工作。父親返回縣立中學上了很短時間的課,後來又在一關一高執教鞭多年,但戰爭結束那年秋天到第二年春天他的確無所事事。
但是,那段時間對我這個小孩來說,充滿了無限的快樂。
幾乎每天中午父親都要和我一起燒水泡澡,水槍、毛巾玩夠後,父親胡亂地背誦論語,他反覆吟誦著「子曰:巧言令色,鮮矣仁。」,「子曰:……」,也不知道是什麼意思。如果我也學會背誦了,父親就允許我到廚房的櫥櫃去拿金米糖吃;我赤身裸體地跑到廚房,抓一把金米糖回來,父子倆津津有味地吃起來。
有一天,秋高氣爽,天氣晴朗,父親對母親說:「我要到平泉去看一看」,讓母親準備盒飯,自己也動手準備些什麼。
那個時候父親無論到哪里我都跟著,我想這次自然也會帶上我,但那天父親卻說"不行"。我嚎啕大哭,於是父親終於答應了。。
我們乘坐公共汽車,咣當咣當地在國道上搖晃著前進,在平泉下車後,到達一個宏大的寺廟內。長大後我才知道那是毛越寺。
寺廟內空無一人,博大的院內雜草叢生,一派荒涼景象。父親找到掩埋在雜草中的石碑後,開始忙了起來。他用水桶打來水,將石碑表面清洗乾淨,然後在石碑上塗抹墨汁,貼上一張大紙,用一把像毛刷一樣的東西小心翼翼地刷平。現在根本不可能允許做這樣的事了,但那時父親興致勃勃地用這種方式製作了好多張拓本。
不用說當然包括雕刻有芭蕉的「夏草や兵共が夢の跡(夏天草淒涼,功名昨日古戰場,一枕夢黃粱)」的俳句詩碑。當然,當時的我根本不懂得這些,只顧在一旁玩;但我突然間發現父親躺在草叢中,仰望著天空。父親兩眼飽含著大滴的淚珠,任淚水弄濕草叢。。
我吃驚地走到父親身邊,這是我第一次看見父親流淚。
我怕一出聲驚動父親,屏吸靜氣地注視著他。良久,父親直起身子,一邊撫摸著我的頭,一邊揉著發紅的眼睛自言自語:「這就是士兵們的一枕夢黃粱」。
小時候的記憶僅此而已。
當時父親為什麼流淚呢?他想起自己的亡友了嗎?或者想得更遠,想到了戰爭本身,不由得湧出由衷的情懷嗎?
後來我知道父親的大學時代學的是芭蕉文學,父親曾追尋芭蕉之路,是一個情感豐富的人。不幸的是我上高中學古文時,老師要我們背誦「奧之細道」,很難學。想到這些,我意識到父親當時的眼淚或許正是對自己前半生經歷的反思吧。
戰敗後悔恨流淚的男人們在800年前的奧州照樣很多吧,我想什麼時候將他們的這種悔恨寫成書。
摘自平泉文化會議所資訊雜誌《在東方》第3號
返回到索引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