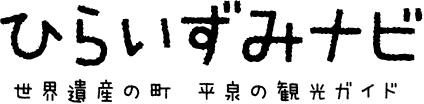兵共梦迹 中津 文彦
我第一次到平泉是1945年的秋天——奇怪的是我竟然记得如此清楚。那是我满四周岁前2、3个月的事,要说不可思议也的确有道理,但我清楚记得这些是有缘由的。
我依然记得战争结束前后的一些零零碎碎的事,或许是因为我童心照样感受到了异样的氛围吧。
8月15日,正是一关的盛夏之际,晴空万里,烈日炎炎。我正在院子的柿树下玩耍,母亲走到我身边,伸出双手抱住我的头说:“你爸爸要回来了,太好了”,这句话嘟嘟哝哝地反复说了好几遍。母亲也许是从收音机里听到战争结束的消息了吧。
在那以后又过了半个月, 9月初父亲复原回家了;那个时代电话、书信往来极不方便,事前也没有任何音信,我还记得一个黑漆漆的男子忽然闪进家门紧紧握住母亲双手的情形。
如今双亲均已过世,也没法考证后来父亲为什么不想恢复原来的教职工作。父亲返回县立中学上了很短时间的课,后来又在一关一高执教鞭多年,但战争结束那年秋天到第二年春天他的确无所事事。
但是,那段时间对我这个小孩来说,充满了无限的快乐。
几乎每天中午父亲都要和我一起烧水泡澡,水枪、毛巾玩够后,父亲胡乱地背诵论语,他反复吟诵着“子曰:巧言令色,鲜矣仁。”,“子曰:……”,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。如果我也学会背诵了,父亲就允许我到厨房的橱柜去拿金米糖吃;我赤身裸体地跑到厨房,抓一把金米糖回来,父子俩津津有味地吃起来。
有一天,秋高气爽,天气晴朗,父亲对母亲说:“我要到平泉去看一看”,让母亲准备盒饭,自己也动手准备些什么。
那个时候父亲无论到哪里我都跟着,我想这次自然也会带上我,但那天父亲却说“不行”。我嚎啕大哭,于是父亲终于答应了。
我们乘坐公共汽车,咣当咣当地在国道上摇晃着前进,在平泉下车后,到达一个宏大的寺庙内。长大后我才知道那是毛越寺。
寺庙内空无一人,博大的院内杂草丛生,一派荒凉景象。父亲找到掩埋在杂草中的石碑后,开始忙了起来。他用水桶打来水,将石碑表面清洗干净,然后在石碑上涂抹墨汁,贴上一张大纸,用一把像毛刷一样的东西小心翼翼地刷平。现在根本不可能允许做这样的事了,但那时父亲兴致勃勃地用这种方式制作了好多张拓本。
不用说当然包括雕刻有芭蕉的“夏草や兵共が夢の跡(夏天草凄凉,功名昨日古战场,一枕梦黄粱)”的俳句诗碑。当然,当时的我根本不懂得这些,只顾在一旁玩;但我突然间发现父亲躺在草丛中,仰望着天空。父亲两眼饱含着大滴的泪珠,任泪水弄湿草丛。
我吃惊地走到父亲身边,这是我第一次看见父亲流泪。
我怕一出声惊动父亲,屏吸静气地注视着他。良久,父亲直起身子,一边抚摸着我的头,一边揉着发红的眼睛自言自语:“这就是士兵们的一枕梦黄粱吧”。
小时候的记忆仅此而已。
当时父亲为什么流泪呢?他想起自己的亡友了吗?或者想得更远,想到了战争本身,不由得涌出由衷的情怀吗?
后来我知道父亲的大学时代学的是芭蕉文学,父亲曾追寻芭蕉之路,是一个情感丰富的人。不幸的是我上高中学古文时,老师要我们背诵“奥之细道”,很难学。想到这些,我意识到父亲当时的眼泪或许正是对自己前半生经历的反思吧。
战败后悔恨流泪的男人们在800年前的奥州照样很多吧,我想什么时候将他们的这种悔恨写成书。
摘自平泉文化会议所信息杂志《在东方》第3号
返回索引页